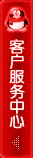活袍之谜
神秘的活袍与阿昌族文化传承
阿昌族原始宗教的最高祭司被称为“活袍”,主要从事祭神送鬼等宗教活动。活袍的传承,分为“阳传”和“阴传”两种形式,其中,“阴传”尤其神秘。
历史上的阿昌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精髓大多以祭祀歌和叙事歌的形式,由活袍在祭祀活动中唱诵得以代代相传。
随着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阿昌族传统节庆、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古阿昌语的使用正急剧衰变。任何文化的传承都需要一个浓厚的语言环境以及对本族传统的认同,阿昌族文化概莫能外,仅凭硕果仅存的活袍独袖善舞,已然凸显不出其灵动之美。
由于历史原因,至今在我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不同程度保留着原始宗教信仰,因而也就有了原始宗教祭司的存在。例如景颇族的“董萨”,哈尼族的“贝玛”,彝族的“毕摩”,纳西族的“东巴祭司”,还有阿昌族的“活袍”,他们在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宗教民俗活动中仍发挥着作用。
和一些少数民族一样,如今的阿昌族文化,包括活袍文化,也面临着不小的冲击。
揭秘活袍
活袍也被称为“无字经师”,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智者。
我国阿昌族人口仅3.8万余人,主要聚集在德宏州的陇川县户撒和梁河县九保、囊宋3个阿昌族乡。
阿昌族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是我国西北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早在先秦时期,由于部落间的征战,部分羌人就开始从西北高原向南迁徙,到汉代人数逐渐增多。大约6世纪初,云龙阿昌部落的头人早慨战胜了蒲蛮部落的头人底弄,成为云龙地区各部落的首领,自此唐宋两朝,云龙成为阿昌族先民主要的居住地之一。
由早慨统一云龙各部落开始,阿昌族逐渐形成统一民族,走向昌盛。而农耕时代的到来,也使得阿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有了新的发展,在原有的自然崇拜基础上,又萌生了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意识,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云龙时期也是阿昌族口传文学逐渐繁衍、趋向丰富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民族学、民俗学学者赵橹、杨知勇等人就曾提出,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先进的南诏文化流入云龙地区,同时汉人、白蛮不断迁入阿昌族聚居地,行商获利,阿昌族先民渐失本土,他们一部分留在原地,与内地迁来的汉、白等民族融合,不断接受其先进文化;另一部分阿昌族则沿澜沧江下游向西南迁徙,跨怒江、高黎贡山,至元明以后,渐次定居于今天的保山、腾冲及德宏境内的梁河、陇川等地。
现实生活中的活袍为人们驱邪治病,主持各种婚丧嫁娶、祭祀节庆。活袍不但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还精通本民族的古阿昌语,掌握着大量阿昌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也被称为“无字经师”。阿昌族民间文学的精华就是由这些“无字经师”进行丧葬仪式和一些重大祭典时,通过诵经的方式传承下来。他们不仅是阿昌族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保存和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智者。
在梁河县阿昌族聚集地,活袍传承分为阳传和阴传。阳传一般由一个活袍带两个徒弟,当活袍去世后,可由两个徒弟中的一个继承;阴传则非常玄妙,被视为活袍传承的正统,一般在宗族内传承。当老活袍去世后,他会通过阴灵选定继承人,并通过类似“托梦”的形式对其施加影响。有的此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继任者,他们心无旁骛地生活,直到某天生了一场怪病,病痛甚至持续两三年,去医院查不出大碍,但却浑身乏力,人瘦到皮包骨头,行为也变得异常。
曾翻译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的阿昌族著名学者杨叶生说,他见过很多类似的情况,一个正常人无缘无故变得怪诞起来,一米多高的祖先牌位飞身就跳上去,然后坐在堂上,让全家人给他磕头;有时在路上与人相遇,也会故意去碰撞对方,令人不寒而栗。这时候一些有经验者便知道其中玄机,遂请其他活袍开坛问卦,方知是前任活袍选定了继任者,遂安“活袍位”,继承活袍衣钵,病痛自此烟消云散。
当继任者病好之后,便具备了活袍所拥有的通神法力,甚至此前一窍不通的语言也能够在祭祀时运用自如。对于杨叶生这样严谨的学者,至今无法解释一些现象,例如一些活袍平时并不会说景颇话、傣话,但每当他们主持祭祀时便会说,据杨叶生在多场祭祀现场观察,活袍主持祭祀时并非想象中的“跳神”,行为举止并不会失态,他们手拿扇子,沉浸其中,很有礼数。
“阿昌族的观念中,一旦被老活袍指定,是不能拒绝的,这就好比天命,如果抗拒,性命都有可能不保。”杨叶生说,“阴传活袍一般是在宗族内传承,但各姓氏的传承又会有区别,有的是连代传,有的是隔代传,有的是隔两代传。例如,曹家有隔代传,也有连代传;杨家现在是连代传;赵家则是隔两代传,赵家的大活袍是赵安贤,他是公认的阿昌族”法力“最高的大活袍,此人于1997年过世,目前这一支活袍的传承人还没有显现。
活袍是阿昌族的精神领袖,他们记忆力惊人,品德高尚,律己行善。已逝的大活袍赵安贤,之所以“法力”高强,与自身的修为不无关系。杨叶生说:“我所接触的赵安贤生活起居非常规律,他不吃腥味,羊肉、狗肉、黄鳝、泥鳅从来不沾,与家人吃饭时要用公筷,而在日常的行为规范上则表现得温文尔雅,不三不四的话从来不说。”
非遗传承人
从12岁到36岁,曹明宽得了一种莫名的病痛,后成为活袍。
在阿昌族的传统文化宝库里,有很多动听的神话传说,其中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是遮帕麻和遮米麻的创世神话,遮帕麻和遮米麻是阿昌族最大的两个神,男神和女神。
每年阿露窝罗节,阿昌族都要祭奠创世神灵遮帕麻和遮米麻,由活袍诵经、赞美阿昌族创世神灵造天织地、创造人类、补天治水、降妖除魔、重整天地、播撒幸福的丰功伟绩。此外,在其他一些祭祀活动中也会念诵《遮帕麻和遮米麻》,例如在举行祈神、驱鬼、祭寨、祭谷魂等民俗活动时,唱诵《遮帕麻和遮米麻》的“降妖除魔”段落;在百姓起房盖屋、娶亲嫁女的寻家谱仪式中,唱诵《遮帕麻和遮米麻》的创世段落。
唱诵《遮帕麻和遮米麻》必定要用古阿昌语,同时使用一种独有的腔调,当地人称“活直腔”,这种唱腔专属于活袍,只有在祭祀时才能用,如若平时使用便是对神灵的不敬。2006年,阿昌族创世神话《遮帕麻和遮米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曹明宽成为国家非遗传承人。
九保乡勐科村龙塘村民小组距离梁河县城大约20分钟车程,一段柏油路之后,拐入一条土路便来到大活袍曹明宽的宅子。进门的正堂摆放着祖先牌位,右边厢房的墙壁上用玻璃镜框装裱着一张光鲜的照片,曹明宽身着民族服装,身披绶带,手拿非遗传承人证书,站在天安门前。那是2006年,阿昌族创世神话《遮帕麻和遮米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他作为非遗传承人去北京领证时拍的照片。
曹明宽生于1943年,家里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老三。12岁以前的曹明宽生活得无忧无虑,他清楚地记得12岁那年,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太平,以后的日子小病不断,莫名其妙发烧,有时浑身乏力,昏睡不醒,但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好像具备了某些通神的能力。这种莫名的病痛一直折磨他到36岁,彼时,曹明宽生了一场大病,他不思茶饭,人虚弱得连坡都爬不上去,于是去县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却又正常。家人请来活袍指点迷津,占卜之后料定曹明宽就是活袍传承人,按照传统,如将老活袍祭祀用过的道具放在继任者头上,顺势敲3下,如若不倒,就预示着继任者可以出师。于是活袍在曹的头上敲了3下,道具果然屹立不倒,由那时起曹明宽正式继任活袍。
上世纪90年代,曹明宽工作于林业局,主要职责是管山护林。一次林管所老所长家的牛丢失了,半个多月都没找到,老所长找来曹明宽占卜牛的去向,曹告诉老所长,你家的牛过河了,去到另一个乡镇,要转3个弯才找得到。按照提示,老所长果然在一个邻近乡镇的寨子找到了丢失的牛。曹说:“丢失牛的日子和时辰一定要记得准,然后做个仪式,请天师来问问,之后通过卦象就能知道牛的去向。”
不仅在本族中主持祭祀,一些邻近的傣族和景颇族寨子、甚至缅甸南坎也会请曹去“开门”(看风水)、“送鬼”(超度),一个现象就连曹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曹只读到小学3年级,汉字识别率较低,也说不来景颇话和傣话,但每次去这些寨子,只要祭台布置妥当,他就有如神助般使用相应的语言主持祭祀。祭祀完毕之后,先前那些景颇话或傣话自己竟讲不出一个字。与此同时,祭祀时使用的是一种专门的活袍调,或称活直腔,属于一种念唱形式。曹说:“那种唱腔我也只能祭祀时才会唱,要把仪式摆好了,把先师请出来,才会念,平时叫我念活袍调我不会说。”
语言环境缺失
现在很多阿昌族人不说阿昌语,或不会说阿昌语。
从梁河县城,沿一条平整的柏油路车行3公里便是九保阿昌族乡永和村委会,阿昌风情园就伫立于路边,它落成于2008年,是阿昌族民俗文化的浓缩精华。宽阔的广场上设有阿露窝罗节的白象标志、遮帕麻和遮米麻纪念馆以及永安司古庙等建筑。上午10时许,风情园内一片静谧,进门的右手边挂着一块牌匾——“永和村阿昌族织锦文化产业合作社”,几名阿昌族妇人轻言细语,手中编织着阿昌族传统工艺品“织锦”。往里走是具有阿昌族建筑特色的峨昌楼,旁边伫立着一幢纪念宫,门前的青石纪念碑上镌刻着2006年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荣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走入纪念宫内,遮帕麻和遮米麻两个大神的塑像赫然醒目,神像下方香烟氤氲,墙壁上用青石镌刻着《遮帕麻和遮米麻》传世神话的汉语译文。
全国有3个阿昌族乡,其中两个在梁河,目前全国阿昌族人口约有3.8万人,梁河约占全国阿昌族人口比例的40%。阿昌族没有文字,但有着情节生动、可诵可唱的诗歌、戏剧和神话故事。自2005年以来,梁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收集、调查和建档,同时建立了非遗传习所,扶持传承人开展传承、展示活动,每年都与主要传承人签订目标责任书,年终进行考核。
然而对于梁河这样的全国贫困县来说,缺乏县级配套资金以及非遗保护的系统理论指导,非遗的保护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意识上过度强调开发利用,使得保护与发展本末倒置;而随着中青年外出打工人数日益剧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也面临瓶颈。
在曹明宽的5个孙子中,只有一个对古阿昌语感兴趣,曹明宽对他寄予厚望,但和现今大多数阿昌族青年一样,这个孙子也喜欢外面的新奇世界,高中毕业后便一直在外打工,每次回家,曹明宽都会迫不及待地让他接触古阿昌语。曹明宽的观念是,古阿昌语是阿昌族文化的灵魂,传承阿昌族文化不能仅仅依靠活袍,必须得有一个浓厚的语言环境。但现实情况是,随着各种现代传媒的强势冲击,传统阿昌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变,新一代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说阿昌语的人逐年减少。
曹明宽有时会接到一些阿昌族同胞打来的电话,说接待客人时,一些阿昌词语不会说,于是在电话中向他请教。曹明宽说:“现在很多阿昌族都说不了阿昌语,这很丢脸。”
粱兴维,回龙生态茶业公司经理,纯正的阿昌族,但他现在已经讲不出纯正的阿昌语,顶多只能听懂大概意思,还必须在语速较慢的情况下。粱兴维说,他所在的梁河县河西乡是一个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用阿昌语交流,而阿昌服饰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或喜庆婚嫁时才象征性穿戴。
异化边缘独舞
除了活袍传承民族文化,学者认为,开展双语教学已迫在眉睫。
回到德宏州首府芒市,梁河美食在这里广受好评,但凡打着梁河正宗老字号的餐馆大多座无虚席。凌晨零时许,芒市菩提寺旁的宵夜一条街,一个小伙子正在制作烤鱼,交谈中得知他姓何,梁河县囊宋乡人。小何说,他今年20岁,初中毕业后去昆明上了一个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民办中专,后来在昆明卖过手机,当过服务员,不久前他回到芒市,暂时在朋友开的这家烧烤店帮忙。小何说:“现在阿昌族年轻人基本不用阿昌语交流,有的甚至都不会说。我也只是逢年过节回到寨子,与老人交流时,又会记起一些阿昌语。”当被问到阿露窝罗节的来历时,小伙子只知道是纪念阿昌族的两个大神遮帕麻和遮米麻,记者又问是否知道每次过节时广场上矗立的白象是什么意思?小何则一脸茫然。
除了语言上的逐渐衰变,阿昌族过去与稻作文化相关的许多民俗及生活习惯也伴随现代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而改变,目前仅有阿露窝罗节依然作为最为盛大的民俗节庆,传统的撒种节、尝新节、祭田公地母已日渐淡薄。
目前除曹明宽外,阿昌族阴传活袍还有3个,分别是曹连文、杨发云和梁其美。不难想像的是,失去了文化的认同以及浓厚的语言氛围,不久的将来,当硕果仅存的活袍们仍然用古阿昌语念诵《遮帕麻和遮米麻》无人能懂时,传统的阿昌族文化又能够走多远。
某种文化的衰落,除了外部环境,也与自身创造力不足有关,保护不是停滞,要在创新中得到延续。有观点认为,阿昌族阴传活袍在维护宗教权威上固然有益,但其传承方式却带有原始的唯心色彩,在传承上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此无论是阴传活袍还是阳传活袍,相互间应抛弃门户之见,在现有保护机制之下,创造条件让活袍开阔眼界,增强与其他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的对话,鼓励他们在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而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双语教学对于抢救阿昌族文化来说已经迫在眉睫。杨叶生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已亡,那么文化和习俗就很快消亡。阿昌族的异化在少数民族当中是比较明显的,有些民族早就开展了双语教学,但阿昌族至今没有双语教学。杨叶生说:“没有语言环境,说阿昌语的人就越来越少,现阶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双语教学,只要教到4年级就永远忘不了。”
- 上一篇:男龙女凤—阿昌族服饰趣谈
- 下一篇:户撒 “三宝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