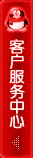远山童话.腊八的忏悔
那棵粗实伟壮的攀枝花树着火了。
习习春风中,满树枝头红霞万朵,争奇斗妍,象火焰纠缠着大树跳跃在枝枝杈杈间。
山火舔嚼过的荒坡地上,腊八妈一屁股坐倒在地,从大芭蕉叶举扬着的凉棚下,捡拾起嬉爬在泥地的腊八,捋起她浸汗的衣裳,凉爽爽地裸着硕大肥白的乳,让羊羔般贪婪的腊八在怀中尽情吮吸、脚蹬手抓地撒欢。
腊八妈一边喂奶一边巴望着攀枝花树桠上,那两只忙忙碌碌的黑雀,早出晚归地衔草筑巢,孵蛋哺儿。她想,天底下草木有情,连禽兽都会养儿育女。我也要竭尽全力把腊八扶掖成人,好让黄泉死界的腊八爹放放心心地在着。
岁月被火热的攀枝花一次次开红,又一次次开老。腊八长得结实高大如参天粗木,而腊八妈却累得弓腰驼背如弯腰的酸杷果树,身姿佝偻枯萎,聪耳失去听觉,慧目成了“雀摸眼”。腊八开始嫌弃她能吃不能做,常常恶语相加。腊八妈苦荞掺饭,眼泪泡汤,残度着枯木朽叶般困沌的岁月。
山前山后的挖沟鸟声声啼叫着,“爹说下,妈莫嫁,煮粥连汤乱过吧”。腊八妈曾在媒人红口水飞溅的撮合中权衡过改嫁,但挖沟鸟伤心悲切的声声啼鸣挡住了她的想法。她想,兴许那鸟就是挖沟坠崖后伸手伸脚地离开了人间的腊八爹转世之灵和托生的信使。
亡夫之信,她得守。亡夫之继,她得续。
腊八在他曾疯狂地吮吸母乳的山地上,挥臂使锄。一只黑鸟悄然飞来,在腊八拾起石块砸去的瞬间,还强行衔走了一条粗黑肥嫩的蚯蚓。腊八手搭凉棚,举目眺望,攀枝花树权上黑乎乎的鸟巢,热闹异常。他以为黑雀觅食哺雏。稍许,那鸟又飞临他身边新挖的泥地土垡间。腊八好奇,便拄住锄杆注目观察。黑雀噉起一只吱吱哀鸣嗖嗖弹腿的蟋蟀就飞,飞到树桠窝巢边,不见雏鸟叽叽抢食,却见一只老态龙钟两眼混浊的老鸟,艰难接饲闭目咽食。
腊八想起寨佬们火塘边的款白。黑雀孝心好,会含食敬老。鸟雀皆如此,人非禽兽。腊八见状,又羞又愧,心如刀绞,连连责骂自己不如禽鸟通情草木懂事。
是日,腊八妈又饿又病仍为腊八做好饷午,她昏头胀脑还拄拐携篮,向山地摸来。山路崎岖,她两腿铅沉,颤颤悠悠中摸索着磕绊着,一跤跌在石板路上昏死了。当她睡醒来,想起儿子还在远山饥饿着,便挣扎撑持起来,一跛一拐地往前跌闯着赶路。毒日头晒着她的头,烈阳光眯着她的眼。忽然,她远远瞅见儿子三步并成两步从山坡上跑来,她以为又要挨骂受打了,心一横,头朝路旁大树撞去……
腊八赶到树下,娘已咽气命归黄泉了。
腊八急着跑来迎娘,本来是向娘忏悔认罪的。可腊八妈却误会了他的本意。他痛心疾首,泪洗泥面,含悔把娘埋在大树下。每日自饮米汤,蒸熟白饭来此祭献。他要让他的妈生不果腹,死后丰衣足食。
狂风暴雨中,一道雷鸣电闪,将那棵大树和腊八劈成了两爿。腊八死了,死在大树底下,身躬膝屈,席地而跪,如对母亲深深的揖拜深深的忏悔。
腊八遭雷公劈斩,寨人的看法是“儿食米油(米汤),母吃残羹剩渣(米饭),罪孽深重,惹怒了雷神爷,招致他雷打火烧,焦糊至心。” 半山梁上,那棵顶天立地的攀枝花树,今年又着火了。满枝满权,红霞万朵,映红了大山里的半个天。
腊八的坟头草,在春光中迎风摇曳,含笑点头。习习的春风,如他的悔恨总是凼凼幽幽地吹个不停。
【原载云南省作家协会《边疆文学》1997年第6期】
作品获云南省第二届(1998年)边疆文学奖作品奖。这是文学奖评委会颁奖词:尽管扛着最现代的摄像机,曹先强也是阿昌的后代。那些遥远的大山里的传说,那些火塘边老祖母悠悠道来的故事,那米酒里酿出的醇醇酒香……已经融解流淌在他的血脉中。小说文字很短,故事很简单,但作者从独特的视角落笔,饱吸了民间文学的精髓,使作品闪现出一种难得的民族特点和野趣。这是通俗和高雅之间的嫁接,这是现代与传统的纽结,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有创意的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