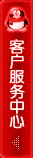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全国获奖散文佳作】
故乡多粘枣。那树,那果,那情趣,长在故乡人的生活,生在我记忆的莽林。为此,我的童年因为故乡的粘枣而写满了金色的欢乐。
故乡的粘枣,高大、富有。在那串清贫的日子里,孤根独树,或立在田头,或树在地脚。其中的两棵,坚实地守住寨门,像一对沉默的老人,风风雨雨,始终如一地站在一起,使山充满一片生机。
粘枣树开米色的细花,挂成串成团的果,粘枣果,初果青绿,熟果通体灿黄,味酸,略带回甜。晚秋,粘枣果满树金黄,人们便端筛拎篓,纷纷相约着踏歌来摘果。故乡人将果生尝也熟吃,拌葱花芫荽或掺胡椒辣子吃;或煮熟刎核留肉质,添香加咸配佐料,做成粘枣糕。粘枣果,在故乡吃法很多,它与故乡人酸酸辣辣的情感纠缠在一起,与故乡人的生活结下了深深的情结。
童年时,粘枣树下是我们的好去处。在那里,童真纠缠着高不可攀的粘枣树,像串串挂满枝头的酸果。我们爱那高高的粘枣树,常常以那两棵树为营垒,呐喊、冲杀、习生、学死。一片火热,一派欢腾。熟果挂枝的季节,灿黄的果串,令人垂涎欲滴。果香诱惑着我们,我们用石块棍棒长长的竹竿,向最厚实最诱人的果串,冲击,扑打,黄灿灿的粘枣,温柔地落在我们的头上、身上。
故乡的粘枣果,故乡人爱吃,故乡的珍禽异兽也爱吃。初冬以后,植物枯萎了。山灵寻食寻到寨边,在故乡,一种俗称破脸狗的野物喜吃粘枣。这使故乡人激动不已,每见粘枣树下破脸狗的踪迹,人们就扛着猎枪提着猎具去猎去捕,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和精彩的故事。
故乡的夜猎是很有趣的。临行前,会掐时(问卜)的要掐时,不会掐时的要请人看卦,种种先兆都灵验了才动身。那神情,那举止,既庄重又神奇,令人难以忘怀。记得儿时,我参与过老叔设计的一次伏击。老叔是复转军人,枪法好,不信卦,但同行的堂兄仍去问了卜。山月,埋在群峰叠嶂中。夜,很黑。我们轻轻来到瞄好的地方藏起来。出门前,老叔说,去时不可鲁莽;堂兄也讲,如掐时不准,猎物先至,一点轻微的响动也会使猎捕落空的。我们猫腰靠近粘枣树,猎物还没来。我们屏住呼吸开始了粘枣树下的夜猎。老叔烟瘾大,常吸得烟熏火燎,连声咳嗽,但那夜却一直不吸烟也不咳嗽。等了好久,等得我想打哈欠了。
突然,前方土坎上,“刷”的一声响,像滚下了一块土疙瘩。猎物来了。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浑身直发毛。那猎物瞻前顾后地来到粘枣树下,东嗅西闻,像发现了异常,磨蹭着不上树。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但仍看清了它。哦!破脸狗!虽称狗却比狗小,实际是只脸有斑纹的大猫。我望望老叔,他纹丝不动。我记起了,他说,破脸狗刚上树,猎击时机不成熟。它要东挑西找,找到满意的果杈才安定下来,手脚并用,左右开弓,像侥幸抓到山寨人的肥鸡大嚼大咽粘枣。那时是它全神贯注忘怀一切的时刻。猎击时机最重要。
粘枣树上,那破脸狗搬枝弄果,悠然自得。我等着,怀间似蹦着只小鹿。我想机会该到了吧!就在这瞬间,堂兄闪电般打出雪亮的手电筒,强光柱直刺猎物的眼睛。猎物双目暂盲,蹲伏树权间,惊呆了。不叫,也不逃。与此同时,老叔举枪扣动板机。枪,不响。再板,再扣,仍不响。破脸狗清醒过来,连滚带爬,跳下粘枣树,便带着风声飞快逃去。老叔堂兄还有我,都很气恼。一看,原来是寒霜露重,老叔猎枪上的纸炮受潮了。
这粘枣树下不成功的夜猎,仅是故乡有关粘枣树的许多故事中,一支小小的插曲。我与老叔堂兄空守一夜,尽管没尝到猎获的欢欣,但我却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狩猎,这次粘枣树下的久久期待。
高高的粘枣树,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枝伸在故乡人的生活中。在绿荫下,妇人缝衣纳凉;男子搓麻笑闹;老者摆古弄经;青年男女依它欢会;孩童们围着它追逐嬉戏。多少风雨,多少晴朗,故乡人与粘枣树,同舟共济,苦度日月,结下了深深的情结。
然而,追寻两棵粘枣树的阅历,许多人说不清,道不白。只有一生光棍爱疯嚼邪讲的王斤大爹讲得出只言片语。他说,那树是雷升火闪野火烧山那年,一对开山始祖初建寨子时所栽。那棵伟岸挺拔的是始祖栽种;那株妩媚婆娑的是始母培植。他还说,成百上千年了,生生死死恩恩爱爱,两棵树像两个人,相依为命,矢志不移。那年,苍天打雷,折断了始祖栽的那棵树的一枝树杈,那棵始母栽的串串疮瘩眼里还流了不少的乳白乳白的泪呢。
【作品原载 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荣获1997年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奖】。
曹歌 2010年11月6日 发布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