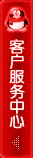民歌:时代记忆 民族记忆一一浅谈阿昌族民歌体新诗歌创作
关键词:文学 民歌 时代记忆 民族记忆
金风送爽,国庆中秋双节同庆。节后相聚,老一辈民族文化工作者,老作家、诗人张承源,给我赠送了两本藏书,一本是民族文学诗歌集《孔雀啊 迎着朝霞飞翔》,另一本是民族文学诗歌集《孔雀开屏迎朝阳》,收到藏书珍品,真是如获至宝。
一
我翻开发黄的诗页,阅读沉寂的诗行,从中选取一组阿昌族民歌,学习借鉴,刊发在此。从两本边疆诗歌集中,感受到阿昌族文学新民歌体诗歌的产生,窥见到阿昌族文人创作者的出现,感受到那个时期文学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以及时光不老,文脉相传,人脉不散的文学情怀。老一辈文学创作者,字斟句酌,朴实无华,文字与诗句中,流淌着诗歌情怀与理想,尽显歌手芳华,充满泥土的芳香。
诗集中,共收录阿昌族民歌7首。作品体裁被统一标注为民歌。其实,这是一种民歌体的诗歌。称其为民歌,它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民歌有区别,民歌是民间文学,作者是人民群众。诗歌是诗人创作的文人作品,此类民歌是时代性大众化文化认识所致,具有特定时代的特定认知含义。为区分两种民歌,我们称诗人创作的民歌为新民歌或民歌体诗歌。
各民族诗人民歌诗歌作品佳作云集此诗歌集,熠熠生辉。其中,阿昌族民歌作品,令人耳目一新。首见一首民歌是1961年桦梁创作的《梁河阿昌族情歌》边地民族山歌风格浓郁,有一个典型句型,采用民歌式结构,得句“骑马要骑英骏马,爱郎要爱农业郎”。此民歌发表至今已六十年时光,作者桦梁是谁一时难以考证。
第二首收入的是1962年孙家绅、李发祜收集的《杨柳曲》,是反应农业春耕勤劳致富的民歌。孙家绅是阿昌族第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作者。他是梁河县杞木寨公社湾中大队人,现今行政区划撤并乡镇隶属芒东镇湾中村上寨人,他是阿昌族群体中参加民族工作队较早之一,五十年代末曾先后到内地民族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培训。火热的边疆工作与劳动生产中受到文艺创作启发,蒙发了他赞美新时代,歌唱新生活的创作冲动,拿起笔杆来,从记录山歌,收集民歌,记录整理民间故事,写作民俗风情文章,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创作始于1960年前后,在阿昌族文学创作者群体中创作最早。他的诗歌作品《愿我的歌》《双铧双犁诉苦》是阿昌族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他与另一名阿昌族作者曹国翠的诗歌,在1965年前后先后发表,同时代早期创作的一些新民歌,作品洋溢着生活气息,发表在《团结报》(今名《德宏团结报》),这是讫今能见到的阿昌族作家文学最早的诗歌作品。这些文学创作开创性填补阿昌族文学发展的空白。孙家绅,也见写孙家申孙加申,今已八十八岁,祝孙老耄耋之年,寿比南山,百岁安康。
第三位收入阿昌族作者藤茂芳,1973年创作民歌《精心打刀送北京》,1977年创作民歌《颂歌飞出心窝窝》。民歌感情真挚,诗句清新,主题鲜明,充分利用民歌善于表情达意的倾诉功能,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藤茂芳是陇川县户撒公社芒东大队人,他曾是生产队打刀工匠生产能手,被抽调至陇川县民族刀具厂工作。长期在农村劳动生活,他在阿昌族民间文学海洋中,吮吸丰富文学营养,也是从收集民歌,整理民间故事开始,走向诗歌创作的文学之路。曾参加县文联州文联,省文联省作家文艺家委员会。他作为省作协会员,曾先后到昆明北京参加文代会作代会,受到文学界领导与作家诗人教导,他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作品,受到读者欢迎,广泛见诸于报刋。
1994年4月笔者与诗人曹明强曾去户撒阿昌族乡芒东村采访,探访重病中已无法语言的民族诗人藤茂芳。不久,藤老去世,我们永远缅怀与铭记文学先辈开创性的贡献。
另外三首阿昌族民歌,有广泛流传的社群基础。特别是阿昌族民歌《阿昌有路走》,俗文搜集。作者署名俗文,真实姓名,已无从考稽。这首民歌体新诗歌,在普遍传播中受到大家欢迎,被传习者不断增删修改润色,又出现内容大同小异的多个版本。各版文本,均见诸于各类型诗歌集、文学作品集,乃至收录入那个时期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阿昌有路走》,句型长短不齐,强调口语化,民歌性强,朗朗上口,诗句流畅,节奏韵律感强,易记忆,易朗诵。采用新旧对比手法,上一节用“想从前,阿昌吃尽人间苦”,控诉旧社会苦难深重。下一节用“到如今”因为有了伟大领袖,有了救命恩人。诗歌排比与罗列新社会阿昌山乡发生巨变的诗意描写,表现“看今朝阿昌多幸福”,再次强化紧扣“想从前,阿昌吃尽人间苦”的环扣与诗性复沓。首尾呼应,上下紧扣。这个手法,使整首民歌形成前后两阙,强烈对比,充分表达诗人鲜明的爱憎思想。
周立整理的两首民歌,《站在茶山望北京》周立整理,《阿昌人民学大寨》周立整理,风格相似。作者署名是周立,笔者打听过文化界前辈们,没有下文。显然是署名笔名。从作品看,作者应该是文化人外来干部,抑或是上山下乡从内地大城市来边疆插队落户的老知青。从诗歌用词遣句,整体结构,赏析主题与艺术特色看,两首诗作文人创作风格明显。诗歌中活套地镶嵌入阿昌族民歌元素“切歌”“切扎”。这些民间歌名,曲称,唱词,腔调,是当时民间文学采风收集到的乡村民族文化资料。能够灵活有机地组件与构造,不显生硬,是当时比较盛行的文坛规范,与大家比较推崇与互相采用的标准文本。切歌,切扎,是阿昌族一种民歌。含义解释有望文生义之嫌,今天听来仍然感觉与原义有些生硬与疏离。
《孔雀啊 迎着朝霞飞翔》《孔雀开屏迎朝阳》诗歌集,主题鲜明,时代感强烈,极有代表性。诗歌集中,这组阿昌族民歌,共有七首作品。时代背景,创作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特殊时期,以那个时代特殊的叙述方式,抒写了特别的诗者感情,抒发出激情澎湃的群体感受,无凝这样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他们抒写了真实的时代生活,抒发了真实的时代感觉。从文学创作与作为时代歌手的诗人站位与视野来说,这些诗句,无凝都是那个时代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当时能登上诗坛,在文坛可见到的最好的阿昌族诗作。是阿昌族文学创作发展重要的弥足珍贵的代表作。
诗言志,歌言情,文学创作者,作为那个时代背景的先锋,时代的歌者,为生活讴歌,为时代写作,他们无愧于心,无愧于使命,唱出了对新生活的无比热爱,表达了对新生活的无限深情与热情向往。他们所创作呤唱的诗歌作品,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那个时代强烈的铬印。囿于所处时代性局限,诗人在直抒胸臆的抒写抒情抒怀之中,难免激情澎湃而诗绪汪洋,意念夸张,豪情在胸而词穷句屈,猛句乍泄。后来人就不应再去脱离时空与时代背景,脱离文学创作的历史横切面,不顾时代语境,吹毛求疵,苛求诗人们的诗句直白、肤浅、滥情与诗情粗糙。
时光记忆,民族记忆,感谢那些有名的或无名的作者,农民诗人,民歌手,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为阿昌族抒写历史,讴歌时代,赞美生活,为阿昌族文学创作,开天创地,填写空白。他们是阿昌族当代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创作,向作家文学转型,向文人文学发展的真正的开路先锋。为我们呤唱下了第一首诗歌,抒写下了第一篇散文,创作出了第一篇小说,拍摄出了第一部电影与电视剧。百舸争流,百业待兴。一批又一批民族诗人,一批又一批民间歌手,一批又一批文化文艺文学工作者,薪火相传,传承根脉。许多人虚心好学,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勤耕苦读,几十年如一日,淡定静默中做出许多突破性历史性贡献,这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使命与担当。
时光匆匆,古老又年轻的阿昌族,千百年来,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填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无数空白。在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进取,勤耕苦作,善于学习,善于发现,善于表达,创造出造天织地的创世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锻制出中国三大民族宝刀的户撒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培育出被称誉为“水稻之王”优质品种“毫安公”,“老姑太”“谷期”农耕文化自信的古老民俗,传承古今,享誉中外。
百年启航路,奋斗新征程。赓续传统,传承经典。前仆后继,继往开来。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已站在两个百年历史性交叉口,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图强,砥砺前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迢迢征途上,我们仍然有无数空白无数空格无限空间需要更多更新更强更专业的人才济济去奋勇填写。
二
赠送这两本诗歌集作家诗人张承源,六十年代末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糸,文学功底深厚,创作经验丰富,有较高文学专业素质与文学素养。八十年代初期认识,把我们当文学新苗培养,希望各民族文学新人不断茁壮成长。从此,书信往来不断,定期收到他们新出刋杂志,偶尔也收到他们新出版惠寄的作品集。当时我正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中文系二年级,他对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帮助很大。可以说是在老作者谆谆教诲,指导,鞭策,鼓励与帮助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和另外一位诗人倪国强负责编辑《孔雀》。我投稿与他们结缘文学,多次书信往返,信中主要讨论作品修改提高。记忆中,有一次编稿时间较紧,他们写信打电话找不到频繁出差拍摄节目的我,刚脆打电报来与我说稿催稿。在电报督促下,作品在州征文比赛,报告文学集征稿,作品集出版中被选录其中。编辑部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做嫁衣,对我的文学创作指导,修改,点评,刋发和编文集,收录我的诗歌,散文,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众多扶持,我获得1997年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1991年3月,张承源在梁河县文化馆参加完《阿昌族当代文学研讨会》,调至省城担任昆明文学院院长。倪国强接班,继续编刊扶持德宏边疆各民族文学新秀。
近年来两老师退休离开编辑部,深居昆明与芒市社区一禺,天崖一方,但文学创作一直把彼此联系在一起。时光不老,文学情缘不散。快四十年时光,彼此仍然有许多交流交往如初次相见。张老师送藏书,倪老师为我新书《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写评论。人在旅途,感恩文学,感恩遇见。在此,深深感谢对文学创作者一直以来给予热心帮助,抬举,提携,培树的所有文学前辈们。
时光记忆,民族记忆,弥足可珍,使族群记忆更饱满,更直观,更亲切,更安暖。让我们共同努力,献给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献给脱贫致富之路上乡村振兴发展变化的阿昌族山乡!
三
阿昌族无文字,仅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民间文学。新中国成立后,阿昌族文学也只是停留在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上,当代文学创作寥若晨星。
改革开放以后,阿昌族中一批中青年人步入了文学的殿堂,活跃在云南省内外文坛,先后发表数百万字作品。孙宇飞以其诗歌《我的筒裙花哟》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曹先强的散文《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其作品还两度荣获云南省“边疆文学奖”。罗汉的短篇小说集《红泪》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紫雾》又荣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孙宝庭的散文集《月亮刀魂》获得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新时期阿昌族文学中,这些作家文学作品,起点高,内容丰富,生动亲切地反应了阿昌族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发展进步的进程。他们为成长中的阿昌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在对本民族口传文化进行搜集、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组织编辑出版了《阿昌族文化大观》《阿昌族之魂》《阿昌族文化论集》《阿昌族民间故事选集》《中国阿昌族》《阿昌族简介》《户撒史话》《梁河阿昌族今昔》《云龙阿昌族史话》《阿昌族春灯实用手册》《神秘阿昌族风俗志·阿昌族》,组织出版了葫芦丝协奏曲《遮帕麻和遮米麻》,拍摄《太阳之子?阿昌族》《阿昌的节日》电视片;拍摄中国第一部阿昌族音乐电视《阿昌欢歌》20首专辑。这些优秀作品赠送给了国家图书馆、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永久保存,在传承与繁荣民族传统文化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曹歌 撰文)
- 上一篇:非遗|阿昌族的口头传承:遮帕麻和遮米麻
- 下一篇:身世神秘的阿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