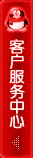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阿露窝罗节 文学专栏】魂系阿露窝罗牌坊(散文)
魂系阿露窝罗牌坊,蹬起的窝罗舞像风在流淌、风在摆动。无数的寻找成了一种难得的眺望。每年的相聚竟是一种伤感的别离,等待竟是每当阳春三月的时候,生活在滇西的阿昌族同胞都要相聚在充满神性的阿露窝罗牌坊下,蹬起窝罗舞,祭奠天公地母。这种春天的聚会不仅让我心灵得到一种慰籍,更让我感受到一种希望的光辉照耀自己,成了一种难言的牵挂,神思飞满美丽的阿昌山寨。阿昌族祭拜天地和神灵的仪式极为庄重,传承了千年的古歌,盘古开天的窝罗调浑厚有力,在《来也要来也赛》和《撒胡赛·撒胡芒》的歌声中蹬起的窝罗舞像风在流淌,造天织地和天宽地阔的史诗彰显出阿昌族始祖高大的身影。这是阿昌族的战神和英雄,母语交织出的生命情感,深深连接着我的梦里梦外。
这种时刻是我最激动的时刻,也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刻。这个时刻,我的目光掠过高高的阿露窝罗牌坊,趁着欢乐的阿露窝罗舞鼓点思绪驰骋在茫茫的天际,心会沿着先人走过的足迹上路。远古的神话,千年的余音不时在我的心间荡漾。因为任何有情感的表达,都不如深深投入激情狂奔的舞蹈节拍那样来得真实和动人心魄。
我站在阿露窝罗牌坊下情也幽幽,思也幽幽,魂系阿露窝罗牌坊,神思飞越滇西莽古大地和茫茫疆野。神思涌动在阿露窝罗牌坊下,我有些忘乎所以。阿昌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不时在我的心间萦绕着。月光倾泻在我的身上,缕缕情丝在跳动,无限的追溯被激起。魂归莽古,千年不变的大盈江水听到了我勃勃跳动的心音,寨子那棵高大的神树——龙宝树深知我的心音。在庄严神圣的阿露窝罗牌坊下,我再一次接受生命的洗礼。阿露窝罗牌坊,那是阿昌族的符号和精神象征,是阿昌族的生命和图腾,象阿昌刀一样立于不朽的心间,它给予人启示、力量和无尽的想象。
阿露窝罗牌坊,它是阿昌族的根!
我是在思索和关注阿昌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渐渐了解到自己民族的,也才慢慢踏上了文学之路的,文学与我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刀砍不断,火烧不烬,风吹不散,雨淋不化。文学作为自己一生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生命的动力和源泉。用心灵浇灌花朵,热爱自己的民族,只有用文学来表达,用笔来倾泻。民族表达与书写,只有发自于感动的内心。
高高的阿露窝罗牌坊充满神性,它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生命里。从它的身影里,我盼到了希望的灵光。有了这些情感,才懂得阿昌族的心路旅程,我才写得好自己的民族。在追求文学不寻常道路上,我在心里供奉着一只牧笛,供奉着一座雕像。孤独的时候吹响它,让自己驱除无数的烦恼,让笛声穿透漫漫长夜,然后为自己奏上一曲远征的歌。文思快要枯竭的时候,我的心会走近阿露窝罗牌坊下,去寻找梦里的那些失落。
文学创作需要激情和梦想,来不得有半点的敷衍和骄傲,要想感动别人,首先得感动自己。作为一个忠实的民族文化守望者,要想深入地写好自己的民族,只有走进民族的内心。一个民族的内心其实就是那一片生长的泥土和子民,就是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独特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连自己的民族文化也不关注,很难想象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会有什么多大建树。
文学需要梦想,更需要几分疯狂。就因为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在造天织地的同时,过于粗心大意,将文字忘记造上,我只好在纷繁复杂的的文学天堂寻找光明,毫不犹豫地骑上了一匹催征的战马,对天长嘶,向更高的山峰艰难挺进。其实这个漫长的过程是我历练的过程,并得到了无限的恩赐和洗礼。作为民族文化的守望者,我有什么理由逃脱责任,有什么理由背叛和阿昌神山赋予我的文化脊梁?
能到鲁院学习是今生最大的福气。我用爱,用自己的执著,点一盏明灯不停地祝福着自己,照亮漫漫长路。来到鲁院我才真正体会到文学道路的艰辛与不易,得到了雨露阳光的照耀。这是人生的一个加油站,一个生命的渡口,因为在这里,我的生命又增加了几分重量,生命的颜色又多了几分凝重。
但我的生命并没有结束,我一直伴着月光上路,我依然还幸福地奔跑在文学的路上。永远走不出神性的阿露窝罗牌坊!
作者简介:孙宝廷,笔名文炯贝琶,阿昌族,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委宣传部,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2届中青年作家班高级研讨班学员,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德宏州作家协会副主席,瑞丽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