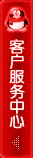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短篇小说】照壁
今年的雨水,真是挂到屋檐上了,大雨,小雨,一场连着一场地下。往年板结的红士坡被雨水淋得松噗噗的,踩一脚都会嗤嗤的响。每天早晨,一出家门,远山近水,尽是一片雾气,湿漉漉的。山野里弥漫着一股阴湿的潮气。
石凤大妈的腰腿骨,尤其膝盖头紧箍箍地疼,成天坐在火塘边烤。老儿子的腰疾也犯了,到处找黑乎乎的那种狗皮膏药。天刚放晴。石凤大妈就拄着竹杆拐走出门来。她总惦记着门前的那堵老照壁淋透了雨,会倒。再说,天色放亮了,在潮湿的雨天里烤火塘,不如走出来烤照壁下的太阳。这样还能好好瞧瞧她数天不见的照壁,能不能挺过这季雨水。
这几天,乡里的人乘刚收住的雨脚。天刚放亮就领着测量队,扛着红红绿绿的标杆、小旗子和望远镜式的仪器,在红坡头上跑上跑下的,到处打桩,到处钉涂画着红洋漆的木桩桩。小木桩子钉到了寨子外头便歇住了,看样子测量队是在为了让那条新路穿过寨子中间,还是绕过寨子上发生了分歧。
老村长还是土改时的那种装束,光着膀子,穿一条白裤头子的大剪裤,腰间挎着一把当地山民进山常用的大头砍刀。他从烟荷包中掏出一撮干燥土黄满是炕梁烟熏味的旱烟,裹卷着,边呵气边说:“绕道走后山,修挖省事。不动田,不坏地,更不损撤房子,但毕竟没有日后车从寨中走方便。”他的话,还是抱着乡干部会上讲的那个老咎咎。测量队姓李的技术员弯下腰又铺展开那张标满了数字、箭头和各种符号的测绘图。他的手间,下意识地捻动着那根一头红一头蓝的双色测绘铅笔。乡文书,石凤大妈的小老儿子,三十来岁,模样挺精,似乎早已“鸡吃豌豆,心里有了数”,又操起了那种文书们最常用的口吻,侃侃而谈。“瓦扎寨,寨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座西向东,迎山开门,顺山势斜坡而坐,稀稀落落的。寨中,一家一户之间跨距较大,沿寨子中间的老古路走,勉强通行。问题只有一个,这条寨中的老路上,不上不下,正好有堵老照壁,像根朽木阻在进山的路上。”
这是一堵古老的照壁。圆滚滚的毛石砌底,四方有棱的土基坯坯打就,凝结着山里人家厚实的希翼,垒砌在家门口上,厚重威严,像一座阴森森的堡垒。
石凤大妈颤颤悠悠地扶着拐杆,站在照壁前,眯着眼睛,寻觅着她家那照壁行将坍塌的蛛丝马迹。这也不能说她守旧。照壁,在这山里人家的门面,历来重要而神圣。照壁的好坏,与户主的地位、名望和家境联系在一起。人们无论家境如何,都要将它砌得规规矩矩,修整得体体面面。家底厚实些的,照壁更是雕龙画凤,气派得很。照壁在人们心目中更主要的作用是它能驱灾避邪,逢凶化吉。因此,照壁在这里很兴盛,很普遍,几乎家家都有,户户都砌,就像家家有个火塘,户户有口锣锅一样。
石凤大妈家的这堵土墙照壁,说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了。如今,猪拱牛蹭,风吹雨打,底部四沿的棱角已磨成了椭圆的碓嘴形,黑亮黑亮的。顶上,没盖瓦,也没上山草。过去,都是石凤大妈割来山草盖压,现在她手脚不灵光了,已有好几个雨水季节没盖顶了。往昔铺顶的陈草,已腐烂变土了,上面长出了几株孤零零的像马耳朵的败园子草,在风中摇曳着。
在石凤大妈的老儿子尖刻地讽骂自家的照壁的当间。旁边,有生闷头吸着烟,德才勾着脑壳,使劲地抠捏脚丫巴里的黄泥。他们虽赞同乡文书,但都木讷地呆坐着,用失神散乱的眼斜瞟着对面山包上的一座新坟。那坟堆里躺着的是石凤大妈的儿子,乡文书的哥,也是有生、德才过去崇羡的人而现在惧怕的鬼。
他叫兴文。有生、德才的好友。早些年,他们听到山下的风声,便决意去找招人当兵的人。但又怕无根无据,人家不理。于是,四个脑壳凑拢来,便合计出到乡里找支书敬酒、敬烟。酒过三巡,支书的舌头大了起来,讲话粗声粗气,四个小伙乘胜又轮流各敬一杯,支书便红着铜铃般大小的眼珠,打着山响的鼾,醉酒伏在木桌上了。兴文手忙脚乱,接过弟弟摹仿文书写的介绍信条,胡乱地翻找出老支抽屉里保管着的大队部的大印子,戳了个鸡蛋大的章。
翌日,四个人藏着介绍条子,唱着山歌,奔下了红坡头,去让人脱裤子体检验兵。结果除石凤大妈的老儿子,因年岁太小体重不够不合格外,其他三人则过关斩将,样样合格。三张写着德才、有生和兴文名字的红皮纸,从县城征兵办公室被乡邮员背到了老支书的面前。老支书既高兴,又愤慨。他像喜怒无常的山童那样,一会儿骂几个毛孩子邪屁无聊,拿政府的大公章开玩笑,一会儿又夸几个小伙子有搞头,为山寨连中三本红皮证书而欢喜无比。这回该他主动找出酒壶了。他们又像前次一样,几个人围住木桌摆开了敬酒台。
山寨的事情,就像山寨里常刮的清秀山风,无所遮拦,一口气能跑十个洼子九个坡。当酒桌上的竹酒筒里还没全酌上米酒。有生、德才的爹及兴文的娘,便扛着竹梢子,身后尾着哥兄奶弟及围观的人群,气势汹汹地涌来了。乡政府本来就不宽,这可热闹了。老支书挥舞着捏着酒筒的手,左劝右说,浑身是嘴,也说不通。只有石凤大妈默默地注视着大儿子,默许了。
打春了。火红的攀枝花开满了寨前寨后,枝头树杈。兴文,在照壁下,披红戴花,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和猎枪的爆响中,被全寨人的鼓锣声簇拥着走出寨门,跟上前来迎兵的部队及县里武装部首长潇洒地走下了红坡头。
有生和德才,则大失所望,他俩捧着红彤彤的入伍通知书,就像老猫抓着了一个猪尿泡——空喜一场。每见那中看不中用的红皮纸,他们就心酸无比,大骂山野里的苦楝树结的苦果多。
兴文在地里栽下的老瓜籽,还没生出新芽。他就穿着有生、德才做梦都在想的军装,握着锃亮的冲锋枪,在部队照了相,寄来了。
德才和有生尾着父母帮这帮那,卖力地干活,为的是要说服父母,像兴文一样去扛冲锋枪。石凤大妈的老儿子,则每饨多吃一碗糙米饭,为的也是能增加体重,增加他参军的份量,像大哥一样去头载红星,腰扎武装带。他们向往追求,羡慕死了兴文的军装和那种迷人的军人风采。
照壁牢牢地矗立在家门口。石凤大妈总是叨念着,叫儿女们盖盖顶,但而今儿强女大,各忙各的,谁也顾不上它。转眼又步入雨季。石凤大妈总是想,今年的雨水大,而且都是连天雨,这堵照壁怕是捱不过去了。
石凤大妈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山下坝子里就有一条直邈邈的公路,远远地望去就像一条白布带子铺垫在那里。各式各样的车子,身子足有一间厢房大,嗡嗡地吼着叫着,来来回回地滚着轮子跑,就像撵麂子一样,跑过之后,屁股后面还总要掀起一阵神秘的灰土。
石凤大妈和年轻的姑娘妹子们,无论爬山砍柴,还是下坝栽秧,每听见那种嗡嗡的闷响,总要放下手头的活计,驻足举目,看个清白。有几个胆大妄为的妹子,还在内心里算计着,有空子的话,一定要跑到跟前,去仔仔细细的瞧瞧那种不见吃草,也不见撒尿的怪模怪样的车子。
岁月如梭。山里的日子,像门前红彤彤的攀枝花,火红地绽开,又火红地死去。很多年头流水般地淌走了。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石凤大妈却不再是盘着黑辫子,插着亮闪闪的戮头花棍,神气活现的姑娘了。她成了系抠花筒裙和戴高包头的嫂子。而现在她已是步履蹒跚,腰弓背驼,身穿黑腾腾的素围腰裙的老太婆了。当年她们那群曾一起商议着,一定要去好好瞅瞅那种不用牛拉不要马拖的车子的姑娘妹子们,也都已各走一方,没有人知晓她们中间到底有没有人了却了那桩诱人的心事。
树老心空,人老颠懂。石凤大妈已不能再爬高下矮,上山下坝了。她只能领着她的那群孙男孙女们,在家门前的那堵照壁下玩耍。过不多久,孙辈都背起他们父辈曾背过的黑漆小木箱,扛着小板凳上学去了。
石凤大妈在家里帮不上手,闷得发慌。只好走出来,拿着长竹梢子或守晒家里的谷物,或坐在照壁下烤太阳。偶尔,隔壁的乔招大妈、关秀老奶凑过来的话,她们便四平八稳地坐倒在那里,各自从包头上掏出自己的铮亮发黑的牛皮烟盒来,津津有味地拼伙咀嚼那种猩红的槟榔烟汁,回忆她们青春辉煌的姑娘岁月;谈论她们拿得起来放得下去的人到中年;小声小气地哀叹她们如日落西山般的老朽暮年。讲到奇妙之处,她们就张着牙齿已残缺不全了的嘴巴,呵呵地笑得浑身颤抖。
在她们的生活里,山下那条白布带子般的公路上的一切,已越来越淡漠、越来越遥远了。她们一点也没觉察到,在她们脚下的这支大山下,也已有一条新辟的公路,象蛇一样地蜿蜓着朝山寨慢慢地伸爬出来。
兴文在山里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享受了山外太阳三年的抚育后,又戴着大红花回来了。他的一切,仍似磁石一样吸引着有生、德才他们。他们从兴文口里学会了许多好话。像“呵呀!”“是的!”“好的!”“对的!”一连串这样的好话。还从兴文手中学会了许多新鲜事。比如在地上画个圆圈,中间加上十字,在十字的四角画上弧,用石子或短木棍做子,列成双方阵营,互相拼杀的“捉棋”。
山寨的后辈伙子甚至山娃牧童都像着魔一样地围着兴文。兴文也确实没白走大地方三年的宽阔大路。他知道,山寨封闭,人们放置和挂放杂物都往烟熏火燎的炕梁上,和蜘蛛结网的篱笆头上挂放。山寨里来了远客,只能坐在树疙瘩和粗糙的草编古墩。兴文便打起了新主意,他在土墙上掏出几个土洞,人们便学着找到了安放物什的地方;他用木板子拼钉上四根条子,寨子里就兴起了打钉平稳舒适的板凳,客人的酒茶,也放在了过去只有乡政府里才有的木桌。尽管那桌凳笨拙古朴得像出土文物,但德才他们是亦步亦趋紧跟着兴文的脚窝窝走。就连寨子里的小娃娃,也受兴文的启发,缠着大人赶街时往山上背电油(电池)玻璃球(1.5V的电筒灯珠),用一根细铁丝就把火亮虫(萤火虫)般的亮光点燃了,弄得许多人,莫名其妙,直呼那是鬼火。
有一件事,有生和德才们还来不及学。那就是兴文看着家里的老灶太吃柴。太浪费。他便说这种老灶成百上千年了,仍没改过样,我们虽然守着山林子,但这种家家都养着的老灶眼,就像一只只大块吃肉的老虎嘴一样,胃口大得像无底洞,多大多宽的柴山,也抵拦不住。
那日正午,骄阳似火,特别烫人。兴文穿着在山寨只有复转军人才有的那种火红色的褂子背心,高挽着裤脚,背着信奉家有家神,灶有灶君的大人,动手拆了他家的老灶台。然而新砌的灶台却缺着个口子。无奈,他便把主意打到了门前那堵老照壁上。他将照壁边上一段斜码着的墙上的土坯迁搬下来,砌垒新的灶台。新灶台砌好了,古照壁倒也没严重损伤。
这一天,他成功了,也为此失算了。这是后来那些胆大妄为而又信神迷鬼的人,惋惜地摇着头评定他的话。兴文病倒了。发烧,发高烧,昏迷不醒,满嘴胡话,一躺就是数月。山寨德高望众的“活袍”被请上了正堂,家人打来一碗米,石凤大妈备好了一炷香。“活袍”手拿米碗,围着兴文头顶,绕了三圈,点燃纸火香柱,放在碗上,用三根彩线吊起一把口子朝上的砍刀,慎重地请师,然后严肃地询卦问卜,其结果是全寨里的大多数人都满意的。那就是兴文拆古老照壁,遇到了过路的孬鬼。当然,兴文还拆过老灶台,灶老爷也很多心,很不满意,乘兴文体衰神虚,讲了几句闲话,伤着了兴文的三魂七魄。
老支书领着乡间赤脚医生,后面跟着有生、德才及乡文书,他们不信邪,但投药问医找了山间所有的偏方秘诀,也不见起色,他们也不敢不信了。
兴文,一躺就是数月。终于,有天中午,也是矫阳似火的日子,他起来了,但他却变了个人。初期,沉默寡言,时常在老照壁下发呆,后来他便活跃起来,往山林里冲刺,往大雨中淋浇,深更半夜里,狂呼滥叫。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他叽哩咕噜的自话自言和“卧倒”、“举枪”、“瞄准”、“射击”的指令声及他重手重脚踏跺出来的沉沉闷响……
寨边,那蓬浓密婆娑的绿竹下,石凤大妈的老儿子所展开的那段议论话题结尾了。德才把从脚丫巴里抠出来的黄粘泥,捏成了没有轮子的车。有生闷头咂烟,那袅袅的烟雾缠绕着他,刺激得他眼睛发红。对面小山包上,兴文的那堆新坟,孤孤零零地又闯入了人们那煞费苦心的眼帘。
天外,不时地传来轰隆轰隆的闷响,分不清是夏天的那种山野闷雷,还是挖路点放的开山炮响。在石凤大妈的耳朵里,雷声和炮声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都一样地震得入心口突突地跳。她只觉得,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地多。雨多,雷也多。天气也就特别地阴湿、闷热。夜里总睡不安稳,时常做一些不相干的怪梦。
火塘的火苗,忽明忽灭的。
石凤大妈的老儿子一边搓揉粘贴他那种医治腰肌劳损的跌打膏药,一边用商量的口气对她说:“那照壁反正长年没有拾整,迟早要倒塌的。新路修进山里来,可以把我们瓦扎寨红泥坡上大块大块的鲜姜运出去,还有我们山里成捆成堆的药材、木材、茶叶、山货……。”
石凤大妈 从黑包头上掏摸出那个油亮乌黑的牛皮烟盒,准备嚼烟。他便赶忙接过来,给她打开烟盒盖,敲碎坚硬的芦子、莎矶、石灰等佐料饼。又接着说:“路走寨子中间过,从山下拖很多的机器上来。往后不要脚碓舂米,不屑松明子点灯。再说您老,人老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了,路从寨门前过,往后可以搭汽车和拖拉机什么的,到山下转转……。”
她嚼着烟汁,她的老儿子贴好了他的跌打伤湿膏药片片。他还想说些什么。去年,他随寨子里的男劳力到山下扛有轮子的打谷机,背着饭包下山,把机器绑起来,十个八个地轮换着,扛沉重的机器,吭哧吭哧地扛了三天才扛到了寨脚的打谷场。
石凤大妈的老儿子捏着膏药片装壳壳,背过手来,反捶着他那扛机器时扭挣着的腰部劳伤。石凤大妈也受了感染似地揉搓起她的膝头。她边揉边冷冷地把口里猩红的烟汁,吐到了火塘边的灰土上,尔后,便拿着一根柴棍棍慢慢地拨盖着,似拨盖着她内心的苦痛和烦闷。
老村长戴着一顶竹叶篾编“哗啦帽”,背剪着手,略弓着腰,走了进来。石凤大妈赶忙让他坐在一个兴文在世时装钉的木板凳上。
老村长和石凤大妈是同时代的过来人。他过去从土改起就当支书,一当就是二十年,人们都称他老支书。前些年,上面搞体制改革,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老支书在“三化”中,是老粗老倌,只占一化,改革的结果就只能改作村长了。尽管这样,老村长还是乐呵呵的,石凤大妈对他是历来都比较了解,比较敬重,相处得也比较和善。那些恩恩怨怨风风雨雨的经历,如同昨天的事,每每谈及都还历历在目。
前些年,寨子里乱哄哄的,到处轰轰烈烈兴贴成串成片的大字报,花里胡俏的。石凤大妈家的照壁上,也贴上了一大联。起初,石凤大妈看着那些篾箩大的红红绿绿的各色彩纸上已写满了铜锣锅般大的字,觉得很是新鲜。
第二天,当石凤大妈确知那大串贴在她家照壁上的大标语是“炮轰”老支书的话时,她便生气了。她说,老支书的为人我清楚得很,我可以用光荣军属的名声担保。于是她固执地把那串标语摘了下来,连撕碎了的筋筋条条都全部送到了大队部里。然后她便破天荒地找来一粪箕冒着热气的鲜牛粪,和拌成稀状,掺和上树叶和剁碎了的乱草,捏成那种园饼状的“牛屎粑粑”,粘在了门前的照壁贴标语的地方。这个园饼状的“牛屎粑粑”,晒干以后,是这一带山里人家,在火塘里烤火的比较好的燃料。
那年月惹火了,“抓革命”的人是不得了的事。他们的革命标语被撕毁了,这等于撕破了贴在他们脸上的马列标签,这是伤筋动骨的打击或是反扑呵。石凤大妈深深地陷入了山寨的旋涡中心,他们内查外调。访查了她家五福八辈的成份,都是贫农,而石凤大妈又连蚕豆大的字,也不识一个,没发现什么复杂背景,加上她是光荣的革命军属,也就没什么更多更啰嗦的麻烦。
老村长年寿比石凤大妈要矮几寿。但石凤大妈的经历,他也能竹筒倒豆子般,一个不漏地数落得出来。石凤大妈的老伴,早年是个帮人吃饭的雇农,后来赊了一个马帮,赶马当马锅头走脚。在他力粗气壮的日子里,常年走远脚到瘴疠肆虐的夷荒坝、洋人街。尽管老哥子生得五大三粗,天不怕,地不怕,但石凤大妈从寨脚嫁过来后,却总要为他与土匪强盗和毒蛇猛兽遭遇而担惊受怕,就在大军马上要下来的那年腊月间,马锅头在老远老远的瓦城得了“摇头摆子”病,回来才歇了几天就仓仓促促地伸脚丢下了石凤大妈。
那时石凤大妈的大儿子一岁多,老儿子还在肚子里。石凤大妈在乡邻乡亲的关顾照看下,早一背柴,晚一担草,艰难地熬到了现在。那堵照壁对她有多重要,老村长也清楚得很。石凤大妈过门的那天,为候个吉利的好时辰,在照壁下苦熬了差不多大半个星夜。石凤大妈扳着手指头,数落她那马锅头的归期,当她数来了望眼欲穿的马锅头,当那串清脆的牛心铜串铃,丁丁冬冬地从寨边响来,她就要拖拉着儿子站到照壁下,踮起她那少妇的欣喜的足尖,朝着响鸣着得得马蹄、清脆响鼻和嘎吱嘎吱的马驮子的方向张望。她不能忘怀,每遇马锅头的归期或出门,在照壁下马帮御驮上鞍时的热闹场景。她的老哥子以高大的腰身,威武的神采,站在那里,或立好桩子或扯好把式或抖拍着油亮的马鞍,数豆子般喊叫大骡大马的名字:“海留!”“咪骡!”、“黑狗!”“灶灰!” 那些神气活现的骡马,听到主人洪钟般的高吼,扬头竖耳,立即竖起或粗或短的尾巴。打着或大或小的响鼻,准确地靠到马锅头指定的方位上。
每当石凤大妈搂着幼小的儿子,哺着乳,看着她那个走东跑西的马锅头,偶尔自己安祥静谧地坐在照壁下,津津有味地吸着他的那种大头子烟卷,吐出一串串的烟雾,似才品出了生活的味道。照壁,简直是她感情生活的内核,她人生命运的主宰,心灵与幸福的全部慰藉与依托……
火塘的火,拖着袅袅升腾的青烟,淡淡地升沉着。石凤大妈不时扯着旁边的柴禾添加老柴树根。老村长望着忽明忽暗的火苗出神。在照壁的话题中,他们不能不提及与照壁纠缠不清的兴文,那悲惨的故事,紧紧连接着石凤大妈的光荣与梦想。石凤大妈心照不宣,心潮难抑。老村长饱含深情而又慢慢吞吞地说,“那是砍竹子遇着节,兴文患的是恶性中暑后遗症!与老照壁无关联。……”
夜深了,雨小了。老村长拿起竹叶篾帽告辞走了。石凤大妈夜晚腿脚不灵光,没有送他。只是嘱咐,小心路滑。人老了,硬骨硬帮的,许多事已由不得自己了,石凤大妈对这个理,体会得越来越深刻,理解得越来越具体。
深夜,石凤大妈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她梦见和姑娘妹子们上山去砍柴。伙伴们忽然地背起柴禾就走了。她还没找到捆柴的藤。她找呀,找呀,衣裙、手脚被倒勾刺划破了,血淋淋的。她找到了一棵光秃秃的老古树下,看见几根白布带子一样的老藤,从树桠杈上吊下来。那白布带子般的老藤像古老的葛根像蜿蜓的蛇蟒,她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扯,却见那大树张着许多大嘴,向她伸来。她吓着了,她躲闪,那嘴还是朝她伸。她更惊恐了,撒腿便跑。她跑呀,拼命地跑,跑到一个大山崖边,一脚踩空,掉下山崖去了。她在空中轻如一片鹅毛,飘呀飘,刚要被那根白布飘带缠住。忽然,对面山包上刮来一阵很冰很凉的风,使她在飞沙走石的混沌中,扑溯迷离。最后,重重地砸到了爬满青苔的一块大石板上。她听见轰隆的一声闷响,惊醒了。她动了动自己的手脚,觉得还是躺在床上的。于是,也就是把它当了个离奇荒唐的噩梦而已了。
在朦胧中,她意识到那声沉重的闷响,并非是她摔碰在青石板上的声音,而倒像是那门前的照壁倒下来的沉沉闷响。石凤大妈沉溺在刚才那怪诞的恶梦的惊悸中,也不想起来看看究竟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是天意。她换了一个睡姿,舒展舒展了麻酥酥的腿脚,又进入了梦乡。
清晨,小孙子背着小书箱,咬着粘饭团才刚出去,又慌慌张张地折回来了,嘴里惊叫着“照壁”、“照壁”。“奶奶,你快来呀!”。
石凤大妈拄着她那根腊黄腊黄的竹杆拐,慢腾腾地走出来。门外强烈的阳光,刺激得她双目有些晕眩。那照壁果真倒平了。原本的威峨高昂没有了。在古老照壁的那个古老基座附近,一大堆散乱的碎泥杂土断土坯,七零八落。土堆上,冒着雨后腾腾的热气,那几株孤零零的马耳朵败园子草,绿叶埋在厚厚的碎土烂泥中,白花花的草根须须裸露在外面,吊挂着几颗晶亮晶的水珠。
东方,一个草古墩大的太阳,从厚重的大山顶上升起来,周围罩着一个簸箕大的眩目的圆光环。太阳底下,山峦沟壑,起伏波动,风起云涌,犹如石凤大妈背着沉重的谷物山货,弓着腰爬山的背脊。那轮廓格外清晰,格外明朗。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文学月刊1991年第8期】
- 上一篇:远山童话.憨爷
- 下一篇:没有下一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