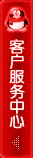火塘
在我的山寨,火塘是精神是旗帜。
走进苍茫的大山,凭借火塘的昭示,你会感悟,在这大山深处,有一条供你演绎的哲理: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火塘;哪里有火塘,哪里就有希望。的确,关于火塘,山寨立有许多的古老规俗。人们兴业庆典、商讨大事得有火塘;村寨宗族家大业大需分户了,得先分火塘;男女情爱欢会得要围坐火塘;宾客临门得升火塘;绝交反目不欢迎来访者得搅灭火塘;举寨欢舞祝酒对歌更得有火塘。凡此种种,火塘与山寨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它点燃的不仅是希望,展示的不仅是理想,它挥舞着的是我的山寨我的民族坎坎坷坷的人生轰轰烈烈的舞步和痛痛快快的关于明天的性格与硬铮铮的誓言。
火塘是我山寨的脚窝我民族的历史。
山有多高,它有多高;水有多长,它有多长。
自从长喉结生红胡子的始祖母和吊硕乳甩赶山鞭的男始祖合谋,在石磨盘滚山的隆隆轰响中,阴阳雄浑地撞击,分娩出嘤嘤啼哭的火塘,我的民族就有了太阳,我的山寨就有了月亮。于是,我的祖宗我的先辈脚底板翻天了发痒了。用背山的背脊背着沉重的火塘满目疮痍的火塘,剽虎唱粗犷的猎歌,跺脚蹬舒心的“窝罗”(古歌舞),将祖祖辈辈的生生死死的恩恩爱爱的酸酸辣辣缩写成一部锈迹斑斑的历史,铭刻在火塘的那串足窝里,抒写在火塘的那杯笑靥上。
地老天荒。阿公的阿公说过,阿祖的阿祖唱过。在火塘的瞳仁之间,曾经豺哭,曾经狼笑,曾经青面獠牙发疯,曾经满山的毒菌开着美丽的鲜花。在火塘的摇篮旁,曾经苍鹰抖举利翅,曾经猛虎舞扬凶爪,曾经恶雨如注,曾经山火烧红天际,曾经魑魅柱着拐杖,从坟茔里爬出来,张着血色的葫芦口无情地揉搓深情地唱歌。阿公只好用弩弓支撑着倾斜的窝棚倾斜的历史,去捡回阿祖的那些黑色肋骨,烘烤出壮丽的火塘美丽的神话和我们生生不息的图腾与渴望。山高路陡,围绕着亘古不灭的火塘,倒下一簇簇大写的鬼,站起一个个血淋淋的魂。
火塘是我山寨的梦境我民族的太阳。
自从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火塘就没有轻松过。领着生生不息的使命和盎盎不灭的妊娠期,牵扯着我的父辈和我的父辈们的撵山狗,在苍茫的传说中苦苦跋涉痴痴追寻,从这山脊的指尖起步到那山梁的脚窝驻足,走过风走过雨,走过蛮荒的雨季,走过蒙昧的炊烟,走过了九山十八洼,才走进了今天。火塘既古老又年轻,它的火焰正红正旺正相当。
在火塘边繁衍,在火塘边生息的我的民族我的山寨,扛着火塘给予的光辉,追赶金色的太阳。日子越烤越暖,生活越烤越香。在暖暖的山寨香香的时代里,山寨在火塘边又设计着一串串新鲜的故事。人们在火塘边品味丰收的年景,编织如诗似画的祝赞,吟哦那米酒般醉心春茶般回甜的爱情。火塘醉了,火塘溢满了快活。
然而,火塘毕竟已很古老很沉重。站在山前,新的世纪风和暖地吹拂着,火塘感动得流泪了,不时溅起啪啪作响的火花。尤其,山寨逐步挂上水电翻阅的新日历,火塘的使命也就撕去大半。火塘,真的老了。
我生在山寨长在火塘边,火塘给了我许多快活的时光连同坦诚的人生,久违火塘,心里就有许多许多的牵挂。初秋,我因回山寨拍摄火塘文化,回望火塘火热的喧腾繁闹,目睹火塘已越陷越深的孤苦悲楚。我很高兴,也很失落。
今朝,那亘古不灭千秋不息的火塘,在我的山寨我的民族的心底里像昨夜星辰正在渐渐陨落渐渐清冷。它是由攒动的人群日愈瘦弱的山林毁灭的?它是自己自觉赴亡的?
火塘没有悼词,留给我们来写。
我感叹,火塘或许终将要死,但我坚信古老火塘精神不死风骨犹存。火塘的死昭示着火塘辉煌的生。光明之火生命之火与我们同在! 声声叹息后,都市里那迷人的万家灯火,便是千万个火塘的生生不息的切切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