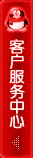阿昌族当代文学:个人叙事与民族话语的现代交界
阿昌族作为边地人口较少民族,其文学向来较少为主流文学研究与批评界所熟悉,于昊燕的文章从总体上述介了新中国成立后,阿昌族书面文学和各种现代文类从无到有、从较为简单到日趋复杂的发展历程。这背后是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建构与个人性相互接榫的带有普遍意味的现代性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陌生文化的认知。
——主持人刘大先

个人叙事与民族话语的现代交界:阿昌族当代文学
于昊燕
阿昌族源于古代氐羌族群,史称 “峨昌”“莪昌”“娥昌”等,是中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2010年人口普查39555人,也是云南的世居民族与跨境民族,主要居住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和梁河县。阿昌族没有本族文字,依靠丰富的口传文学继承传播历史文化记忆,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及大量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民间歌谣等,反映阿昌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与时代风貌,汇融成悠久而完整的民族文化体系。新中国民族政策赋予阿昌族平等的社会地位,普及文化教育,阿昌族长期被边缘化的民族身份觉醒深化,作家队伍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先后有孙宇飞、曹先强、罗汉、孙宝廷四人获得五届骏马奖。
谚云“阿昌生得犟,不哭就要唱”,形象勾勒出阿昌族乐观坚毅的民族性格与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质。新中国成立后,阿昌族学习汉文书写,创作歌颂党歌颂祖国的诗歌。1956年,孙家申《双轮双铧犁诉苦》发表于德宏州《团结报》,是已知的阿昌族作家个人创作的第一篇书面作品。50、60年代,阿昌族诗人陆续发表《唱歌跳舞向着党》《红太阳光辉照户撒》等诗歌,以民族体验与认同的方式向国家话语靠拢。滕茂芳《向着北京唱赞歌》书写“敲起象脚鼓,跳起‘金来过’”的载歌载舞的喜悦情感与“条条江河汇大海,孔雀飞向金太阳”的忠心思想。在阿昌族的传统文化中,天公遮帕麻创造了太阳,太阳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阿昌族生活的德宏州被称为孔雀之乡,民间文学流布勤劳善良的孔雀姑娘的爱情故事,孔雀是吉祥美好的象征;孔雀飞向金太阳把忠于党与忠于民族文化合二为一,感情真挚,充溢民族文化特色。这些诗歌把情意绵绵的民歌形式与时代诉求相结合,国家的忠诚与爱情的心心相印合二为一,时代官方叙事柔化为日常生活叙事。即使是抽离当时的意识形态主题,诗歌中民族化、生活化、伦理化的元素依然保持令人感动的文学色彩,也化解了少数民族群体对原本陌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焦虑感。
80年代初,《党的恩情唱不完》《边疆农村面貌新》《不到花山心不甘》等诗歌依然延续了以“找妹不怕路程远”类比四化建设的浓厚生活气息与原生态民歌样貌。80年代中期以后,阿昌族在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坚守之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诗歌主题转入更深层次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重构与认同。孙宇飞《我的筒裙花哟》“织着一个古老的神话”到“快去接受知识甘露的滋润,来年织出更美丽的彩霞”,主动承担民族发展的责任;曹明强《寻根》“高昂的箭翎划破蓝天/宣告:/只有傲然凸起的乳峰/才能哺育出高原的粗犷”发出源自内心的对民族精神的呼喊。赵家福《太阳之恋》“一张古老的弓已经张满幽闷地嚼食时间/浑然在苍茫的早晨来吐泻万千之剑,劈开混沌透露海底的清晰”,表达对阿昌先祖创世纪的敬意。诗歌把深远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性进程融合,在多元共生的空间格局中,彰显民族价值,深化世界价值立场下的族群认同。
1978年,孙宇飞在《团结报》发表了阿昌族的第一篇散文《园丁的心》,也打开了阿昌族散文创作的大门。阿昌族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多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本民族的传统与现实,承担集体表述的使命和民族文化建构的重任,以民族文化属性建构出独特审美感受。孙宝廷《寻找先人远去的足迹》不仅对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进行散文化重述,还增加了腊亮拯救人类的英雄传说,散文集《太阳之子》讲述了阿昌族“象战”“东吁之战”“木梳之战”“片马之战”“滇西抗战”“反抗之战”“解放之战”等反对土司统治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再现民族历史,坚守民族信仰。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月亮刀魂》《穿在身上的史书》《奇味的过手米线》《阿昌族的篾制茶筒》等器物散文记录了阿昌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阿昌族的月亮刀,这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祭秋神》《祭寨神》等风俗散文记录了阿昌族的节日文化,其中,阿昌族最重要的节日是“窝罗节”,“窝罗”意“在屋旁欢乐”,窝罗节为了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始祖遮帕麻和遮米麻而为民除害、造福后人的功绩。孙家申《阿昌族歌舞〈蹬窝罗〉》、杨叶生《阿昌族尝新节》《阿昌族的传统歌舞“窝罗”》《阿昌族的“活袍”》、赵家健《阿袍的烟锅杆》对“窝罗”进行多重阐释,多层次叙述渗透浓厚阿昌文化气息的故事,表现出 “鲜活的民族生活内容、独特的民族表现形式、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审美风格”,展示阿昌族文化的非遗价值。阿昌族散文不断书写创世纪文化母题、族群的历史变迁、生命经验、生存现实,把民族记忆民族生活浓缩为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构筑民族精神诗意栖居的空间,舒缓现实生活中多元文化裂变带来的身份迷失感,维护民族尊严,凝聚族群归属。
阿昌族小说写作始于80年代,以个人性为主轴,把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在历史的纵深空间中反映阿昌族的生活变化与文化差异碰撞,主动汇入大时代叙事的合唱。阿昌族的小说贯穿着宽容、乐观的精神与质朴、诚实的写作态度,曹先强《弯弯的路 弯弯的歌》如实描述“学大寨工作组”来到阿昌山寨后“开座谈会,开批判会,讲政治,讲形式,讲界限”,“叫“活袍”“稍干”们低头认罪,”开会讲卫星,干活说放卫星“的政治运动。然而,工作组的人与当地阿昌人在劳动中相互帮助,从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到最终与阿昌山民互敬互爱,相互理解,明白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文化底蕴,甚至允许阿昌族的山歌与样板戏相互并存,不仅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还表现了阿昌族的人性之美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融合。与很多少数民族文学在80年代出现的“出走者”形象不同,阿昌族小说塑造了生动的改革者形象,如曹先强《弯弯的山路 弯弯的歌》中的学习新知识追求新生活的腊囡与懒骨头小二、《寨头有棵龙宝树》中的一再尝试种植橘园的们老头的小儿子,罗汉《跛脚荞发》中用现代技术现代理念经营磨坊的复员军人接发,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勇于接受新知识与新的生活理念,改变传统的生活模式,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阿昌族的小说也书写社会转型发展中的阵痛,罗汉《刀匠莫福》讲述了莫福老爹与当县长的儿子之间的矛盾,儿子不仅不学习祖传手艺,还为修公路劝父亲将刀铺拆掉,最终县里为莫福老爹新建一间刀铺,老人与儿子和解,表现了新文化观念、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传统文化的自新。阿昌族小说内蕴着反思精神,在现代思想的烛照下对封建落后文化展开批判,罗汉《蛊女》《姑妈的婚事》描写了被称为“蛊女”的阿昌族妇女的悲剧命运,反映山村封闭愚昧的封建落后思想。密·麻腊的《流亡家族》带有鲜明的寻根文学印记,莽古寨的黑娃追述故乡的悲壮往事与先祖们的灵魂,探寻的笔触突入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对阿昌族的文化根脉进行追寻与自我阐释,展现阿昌族作为边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阿昌族的小说积极尝试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罗汉《紫风》写了阿昌族在工作队进驻村寨到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以魔幻主义的手法表现了阿昌族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今日与往昔、现实与神性间的迷惘与期待,村寨变迁中体现出重构身份的强烈诉求。
新世纪以来,阿昌族与外界社会的经济不平衡、文化差异等非同步性等问题日益显现。阿昌族在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地域等方面有异质性,但并不是纯粹的、封闭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系统。阿昌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互动,受到傣族、汉族民族影响,在语言上形成阿昌—傣或者阿昌—汉的双语系统,多民族共生文化、悠久的史地背景、共享的区域资源,使阿昌族的文学表达成为一个多样性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情感和命运共同体。阿昌族人口少,作家数量也不多,女作家尤少,族内优秀作家的视野、胸怀、思考、审视,成为本民族文学革新与发展的重要源泉。曹先强、罗汉等优秀作家,在丰富创作经验基础上把本民族文化、周边民族文化和国外优秀文化融合为新的文化资源,尝试把民族文化、现实生活、数字化技术、写作模式之间汇融,进行“跨栏”式创新。在题材上,罗汉把自己在民族聚居区以外的生活纳入到文学创作中,比如缉毒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80后90后作家也逐渐跨越族群界限,关注全球化文化汇融背景下的人类生活。在形式上,曹先强与罗汉都进行电视剧剧本、电影剧本的创作,还把博客、微博等作为载体,对阿昌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即时性关注,改变“他者”的固态期待和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从50年代到新世纪,阿昌族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探索、发展与多元化三个阶段,是现代教育推动下的书面文学的崛起,亦是国家书写视野内个人叙事对民族话语的现代性建构及对民族身份的深度体认。
(作者简介:于昊燕,教授,文学博士,任职于大理大学文学院)
- 上一篇:论阿昌族酒文化
- 下一篇:深刻认识阿昌文化价值,树立民族文化自信